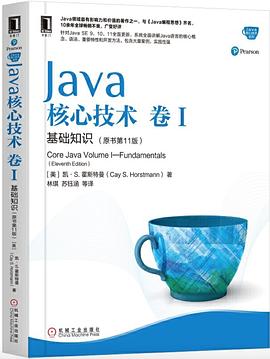读卡勒德·胡赛尼《群山回唱》
我很喜欢卡勒德·胡赛尼的作品,看过他出版的所有书,并且他的书中文版都翻译得特别棒。《放风筝的人》是我看的第一部他的作品,随后他又出版了《灿烂千阳》、《群山回唱》,每一部作品都不落窠臼,令人惊叹。他作为一个阿富汗裔美国人,向世人讲述了阿富汗乱世下各种真实残酷、令人心碎的故事,他的情感该是有多细腻才能写出那么触动人心的文字,以至于我每看一遍摘抄,都会起鸡皮疙瘩。也因为他,我后续去了解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史和阿富汗历史,曾经那么富强的一个国度如今成为一片废墟,真是令人唏嘘。
摘抄
阿卜杜拉无法想像父亲也曾荡过秋千,也曾是个孩子,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孩子,无忧无虑,无牵无挂,和小朋友们在野地里疯跑。父亲,他两只手上是累累的伤痕,他脸上刻满了疲倦的线条。父亲,他好像一生下来就拿着铁铲,指甲里带着泥垢。
想起那次串门,阿卜杜拉记得最清楚的,就是帕尔瓦娜像裹了尸衣一样的窘态。她当时怀着伊克巴尔,呆坐在角落里,一声也不吭,身体缩成了一个圆球。她就那样坐着,双肩收紧,两脚塞在隆起的肚子下,好像要努力缩进墙里,消失不见。一条脏兮兮的面纱像盾牌一样挡住她的脸。她紧紧抓着下巴底下的面纱,把它拧成了乱糟糟的一堆。阿卜杜拉仿佛看到,羞耻如水汽般从她身上蒸腾而起,看到她自觉何其渺小的那份难堪,他心头涌起了一种对后妈的同情,这种感觉让他自己也觉得惊讶。
我发誓,自从看到你的脸,世界就变得伪善与虚幻。花园也困惑,不知道什么是叶,什么是花。鸟儿心烦意乱,分不清哪是食物,哪是诱饵。这是鲁米的诗。
“喀布尔嘛……”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, “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。”
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。虽然频繁光顾医院,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。 “那个小屁孩?小流氓。他懂什么?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。”
她会说,你很幸运,帕丽。你不必太努力工作,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。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。太漂亮,只会把事情搞砸。她大笑起来。噢,听我说。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当然不是了。只是观察。
你在说我不漂亮。
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。再说了,你蛮可爱的,这就够好的了。我向你保证,亲爱的。甚至更好。妮拉 ·瓦赫达提:那是。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。我又喝酒又抽烟,还谈恋爱。谁用数学来反叛呢?
妮拉 ·瓦赫达提:我做的每件事情,布斯图勒先生,都是为我女儿做的。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,倒不是说她不理解,或者说不知道感激,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,我的女儿啊。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,遭多大的罪,要不是我
艾蒂安 ·布斯图勒: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?
妮拉 ·瓦赫达提:布斯图勒先生,我已经相信了,她就是对我的惩罚。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,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,还有什么东西,最让她目光流连。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。一个人影。软,硬,两种感觉相伴而来。软的是一只手,牵着她的手。硬的是膝盖,她曾把脸枕在上面。她搜寻着他的脸,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,它就躲开了,滑出了她的视线。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。她的人生,她全部的人生,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。冥冥之中,她总有这样的感觉。
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,来得既任意,又愚蠢。
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,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,用我的手术刀,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,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,活在这样的秩序下,一次狗咬,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,让她遭到遗弃,成为歧视的对象。
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我想,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。比如说钱,声望,社会地位。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,那就过于简单——这想法也许可爱——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。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,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,不可预测的,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。可是,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、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,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,故事将慢慢显现,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。这个故事支撑着我。
鸣金意思是一种中国古代战争时作战行动信号方式,指停止进攻或撤退。
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。比如,有些早晨,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,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,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、多斑的脚上。他吼我的名字,做出一副婴儿相。他抽鼻子,活像一只周身湿透、胆战心惊的老鼠。我厌恶他这种表情,我厌恶他这副做派,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,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。有些日子,我只想逃开他,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。